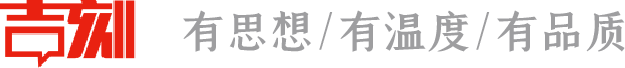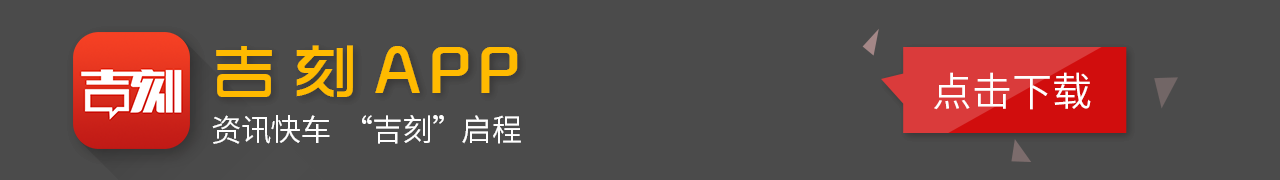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(许仕豪、李丽、吴丽楠)上个月,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仲裁委”)发布工作报告,详细介绍了自2023年2月成立至去年底的业务开展情况。作为全国唯一的、专门处理体育领域纠纷的仲裁机构,仲裁委积极推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设立的体育仲裁制度落地实施——中国的“体育法官”,正在为体育法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。
赛场外的“裁判员”
1995年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首次写入设立体育仲裁机构的条款。2022年,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增设“体育仲裁”专章,明确由国家体育总局负责组建体育仲裁机构。法律的完善,是仲裁委成立的重要前提。
“过去的体育纠纷,往往依赖协会内部解决,缺乏完善的救济渠道。”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韩向飞坦言,在制度空窗期,四类纠纷尤为棘手:协会处罚争议、运动员欠薪纠纷、注册资格纠纷、兴奋剂违规问题等。专业性强、规则特殊的体育纠纷,常因法律程序缺位陷入“三不管”境地。
“假如协会给运动员开罚单,是很难进入司法程序的,这意味着协会处理已经是终局了。”韩向飞说,“又比如欠薪纠纷,运动员的工作合同与普通劳动合同不同,劳动仲裁机构不愿受理,法院又不一定接,往往求诉无门。”
因此,兼顾专业、公平和效率的仲裁制度,完善了体育纠纷的救济渠道,弥补了争议解决的机制空白。考虑到运动员职业生涯较短、赛事不等人等特殊性,体育仲裁时限为常规3个月、(大赛时)特别程序24小时,相较司法程序更加高效便捷,最大程度保护各方利益。
截至去年底,仲裁委累计接收仲裁申请173起,立案审理82件,案件覆盖足球、冰球等六类运动项目。此外,仲裁委还在推动体育社会组织与仲裁制度的衔接,目前已有中国足球协会等4家全国性协会将体育仲裁机制纳入章程,49家项目中心、单项体育协会完成管理规则修订或赛事条款增补。
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卢松说:“过去解决体育纠纷主要靠三个渠道,即体育协会内部的争议解决机制、法院和劳动仲裁。体育仲裁委成立后,相当程度上接替了法院的工作。”作为独立第三方、“赛场外的裁判员”,仲裁委既为运动员提供权益救济渠道,亦促使体育组织完善内部规则,助力行业治理水平显著提升。
案件多为“民告官”
仲裁委公开的数据显示,不少体育仲裁案件呈现出类似“民告官”式的特征。
《2024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年报》(以下简称《年报》)显示,截至2024年12月31日,公民个人作为申请人的仲裁案有55例,而作为被申请人仅3例;对比之下,法人(如俱乐部)作为被申请人的有47例,体育社会组织则有24例。综合来看,涉及体育纠纷时,个体作为仲裁申请人的数量较多,各类组织机构则往往处于被申请人地位。不对等的地位和话语权,引发了个体通过仲裁维权的需求。
类似“民告官”案例存在两个明显特点。一是合同、转会纠纷多;二是运动员很多都是未成年或学生,法律意识薄弱,往往导致维权困难。
此前,某未成年运动员因青训合同纠纷陷入职业困境。俱乐部与其父母签订协议时,设置了一系列包括高额解约金在内的、只有俱乐部可以单方解除的条款;后因家庭与俱乐部矛盾,运动员面临无法转会且被禁止注册参赛的难题。
此案若严格按合同条款裁决,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损,但直接解除合同又缺乏法律依据。最终,仲裁委促成双方“各退一步”达成协议,运动员得以重返赛场。对这样的裁决结果,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袁钢表示:“未来体育仲裁规则修订应更多考虑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。”
“民告官”多,不意味着仲裁委“拉偏架”。实践当中,需要兼顾各方合法权益。某大学生运动员转会后被原属俱乐部和新俱乐部双重注册,引发“一女二嫁”争议,被禁止参加某项全国性赛事。仲裁委在尊重运动员意见的同时,充分考量了俱乐部的利益,最终实现了相对平衡的裁决结果。
“一方面,运动员享有注册与交流的权利;另一方面,俱乐部长期培养运动员成本高,如果运动员成才后就被挖走,对培养运动员的俱乐部的利益损害也很大。”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赵健说,体育仲裁的作用,就是依照法律法规保护各方权利、合理解决冲突。
值得注意的是,足球领域纠纷最为多发。《年报》显示,足球领域纠纷占2023-2024年仲裁委受理案件总数的86.5%。“足球领域案件范围广、爆点多、串案多。”赵健总结道。
仲裁“主权”需维护
体育仲裁首次引发大规模“破圈”关注,当属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审理孙杨案件一事。孙杨最终被判未能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规定,被禁赛4年3个月,引发轰动。专家普遍认为,事件折射出中国体育界对国际规则和仲裁事务了解不足的现实,也反映了中国体育仲裁加强国际交流的必要性。
“一些案件暴露出了国内缺乏专门体育仲裁机制的被动性。”袁钢说,我国运动员及其团队在处理国际体育纠纷时因对体育仲裁认知不足、缺乏经验造成了诸多问题,建立并完善国内仲裁体系,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国际体育法律思维与规则意识。
不少专家还提出,一些外籍运动员或教练与国内俱乐部或协会的纠纷,若国内未设体育仲裁机构,外方多数会移交国际体育仲裁法庭,这意味着我们在相关争议中丧失仲裁的管辖权。建立并完善国内仲裁体系,某种程度上是仲裁“主权”问题。
巴黎奥运会特别仲裁庭12位仲裁员中,亚洲代表仅有卢松一位;另设的反兴奋剂仲裁庭中,清一色都是欧美面孔。卢松表示,当下国内体育仲裁人才力量依旧不足,需要继续学习和对接国际规则,不断培养壮大仲裁员队伍。
“要和国际接轨,包括仲裁机构管理、仲裁员选聘、仲裁规则细化等。”韩向飞说,等发展更为成熟、积累更多经验之后,仲裁委“或许能为中国举办的国际赛事提供仲裁服务”。
在他看来,这是中国体育仲裁大有可为的领域。“未来,我们希望为国际体育纠纷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、中国方案。”
赵健还建议扩大体育仲裁范围,他表示,体育争议具有复合性,往往同时涉及商事、劳动、体育等多个领域,不可能同一个争议分为几部分由不同机构受理。“建议凡是与体育有关的纠纷,当事人之间签订有仲裁协议的,仲裁委均可受理。”
来源:新华网